近年来,各种经典游戏的重制版作品屡屡在游戏界引发热潮,尤以《战神3》、《生化危机2》以及即将面世的《生化危机3》为翘楚。尽管游戏重制之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原汁原味”,但重制行为所带来的诸种问题也使得我们得以以一种对比试验的视角重新审视电子游戏本身:在游戏重制过程中,实现或凸显的究竟是什么?技术上的革新是否召唤了电子游戏内部的乌托邦幽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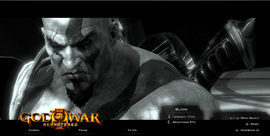 |
 |
在开始我们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厘清基本的概念:首先,游戏重制(Remake)是指以更先进的技术,在保留原作游戏的故事、人物、玩法、关卡设计等主要元素的基础上,重新打造一款游戏的过程,而非以补丁的形式对游戏的本体进行更新;第二,与对文物或胶片电影的修复不同,针对电子游戏的重制本身是一种商业话语 (这其中或许蕴含着福柯所谓“知识考古学”的因素,但并非我们这个时代所能讨论的),是以商业逻辑为最优的;第三,我们说重制而非翻新,是因为电子游戏本身的数字性:当我们说玩家拿到一款重制版游戏时,拿到的并不是一张翻新过的旧软盘,游戏数据包之中也没有一丁点儿旧版游戏中的代码。我们可以说这个过程之中并没有任何实体,取而代之的是借尸还魂。有以上三点作为前提,我想参照罗兰•巴特在《神话修辞术》一书中所做的拆解工作,重新审视当代电子游戏所塑造的种种神话: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它们基于日臻成熟的数码技术,所作出的乌托邦式允诺:“化身为勇不可挡的战士奎托斯,从地狱的深渊攀至奥林匹斯山的山顶,向背叛者展开复仇。”(《战神3重制版》)“探索一个充满着美丽、残暴和神秘的世界。”(《野兽之影》)“诉说你自己的故事。每个选择都会导致连锁反应。”(《底特律:变人》) 。它们虚构了一个足以令玩家沉浸于其中的世界,而这是靠玩家的扮演以及技术上景观的真实来保证的。
 |
 |
我选择了《生化危机2重制版》这部游戏,是因为重制过程最能体现这种乌托邦的进化:我们能从前后两个文本所做出的取舍对比之中,发现什么元素对乌托邦是必要的、必须提升的,什么是有害的,需要予以排除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个文本之间构成了一个对照组。在电子游戏的历史中,《生化危机2》是当之无愧的经典。它是1998年由卡普空公司(Capcom)开发及发行的冒险类游戏,也是《生化危机》系列的第二部作品,由三上真司负责制作。游戏故事讲述1998年9月29日,新人警官里昂来到莱肯市(Raccoon City,又译作浣熊市,是游戏中虚构的城市)警察局上任。但是,在进入市区以后却遭遇了被T病毒感染的丧尸。 同一时刻,S.T.A.R.S.队员克里斯的妹妹克莱尔,为了寻找失去音讯的哥哥也来到了莱肯市,并且也遭遇了丧尸,正是因此,两人阴错阳差地相遇,并在丧尸横行的莱肯市展开冒险,调查生化危机背后的幕后黑手安布雷拉公司(Umbrella Corporation)。
 |
 |
风景不属于游戏性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一款电子游戏中,风景可能才是真正的无用之物。一款现在所谓3A大作在IGN上的评分可能会远低于《超级玛丽》这样像素风格的游戏,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当然,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游戏美学成为了一个对游戏的新的评测维度,但“游戏性”仍旧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如果它曾经成立,那是因为在电子游戏的幼稚时代,游戏功能的简单使得标准也相对单一;但被戏称为“驴友模拟器”的《荒野大镖客2》这种游戏的“游戏性”又何在?“真实”又如何能被称作“游戏性”?
 |
 |
《生化危机》的游戏画面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业界翘楚。为了以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最大程度地实现“仿真”,CAPCOM花费了很多心机:譬如,游戏看上去是全3D制作,其实是巧妙地运用“2D 背景+3D人物”的方式,让开发人员绘制出带有景深效果的 2DCG 背景贴图作为游戏的背景,然后再让3D人物按照制作者原先设计好的镜头角度进行移动。但囿于条件所限,现在看来画面仍旧只能说是粗拙,而且很多场景极为怪诞:比如每次穿过房门抵达下一个场景之时,为了节省运算量,在进门的一刹那屏幕会变黑,只剩下一扇门的贴图和开门的音效,然后再转场进入下一个房间。《重制版》理所当然地取消了这种颇具时代感的设定,取而代之的是玩家可以自由(相对的自由,譬如你无法选择直接离开浣熊市)探索,在办公室和回廊的角落中搜集道具和收藏品。这些改进同样让浣熊市在视觉上更像是一座横遭劫难的城市了,但它真实吗?什么样的警察局里才会到处充斥着令人费解而无用的机关密道?无论是遍地废墟、血肉横飞的浣熊市大街,还是怪诞异常的浣熊市警察局,或是未来感十足的保护伞公司地下基地,这些失真的元素糅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一个拼搭般的浣熊市。整个舞台——或浣熊市的设计,是暴力、悬疑等多种诉求角力之后妥协的结果,而不是为了仿真。这样看来,对游戏内风景的考察结论便呼之欲出了:它提供的并不是真实的风景,而是真实的想象。从阿里斯托芬的《鸟》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乌托邦从来不需要“看上去像是真实的”。这样,无论游戏的主题是赛博朋克还是末世废土,风景都只能沦为附庸,其最大意义在于展示技术的奇观。不像在电影世界中,风景可以为故事提供舞台;游戏中的风景本身就已经是叙事的一部分,不是场景,而是段落。在数码特效大行其道的今天,这一逻辑得以空前凸显:人们不再为了《关山飞渡》的故事而去寻找西部石碑谷景观,而是为了一个故事、一个主题,亲自去搭建一个数码景观。在此前提之下,所谓“真实”便颇值得怀疑了。三、订制色情:游戏的身体与身体的游戏那么,至少电子游戏还向我们允诺了自由的游玩;如果前两个部分还是在围绕游戏本身讨论,那么在这个部分中,我想要探讨不断更新换代的游戏是如何改变玩家的赏玩逻辑的。我想以一场“跨界”为引:2019年,全球最大的免费色情网站pornhub上公布了站内各项数据和内容的年终报告,在本年度的“TPA”(The Pornhub Awards)中,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到各大游戏IP的热度。《生化危机2》中的艾达•王排在第八位——在2019年终,共有1,398,164人次在pornhub上搜索她的色情视频。 没人会怀疑,今日,电子游戏已经成为色情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当然,在本质上,基于游戏而创作的色情同人制品与漫画、动画或电影中的并没有逻辑上的区分,我们也并不在这里讨论这一类。
我们讨论的是在游戏重制过程中对人物的色情性再创作。乔治•巴塔耶认为:“色情体验和神圣性的体验两者均具有一种极端的强度。”这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当电子游戏野心勃勃地想要用0和1书写创世纪之时,相对应的,玩家同样也会试图从这个新世界中发掘色情体验,这两者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我简单梳理与电子游戏相关的四种色情,列举如下:衍生品:这是处于游戏外部的作品,即我所说的同人制品。它们的制作与传播不会对游戏本身产生任何影响。游戏内部软色情:在主旨并非色情的游戏中加入暗示性元素以吸引玩家,比如下文中的《死或生》。色情主题:以纯粹的色情为卖点的游戏。这里可能包括俗称的“小黄油”,也可能包括如《柯南:流放者》这样的大作——在这里,裸身行走和性交本身就是游戏的一部分。主观色情:玩家巧妙利用游戏中的设定来实现色情的目的。电子游戏何时与色情扯上关系?这个问题目前难以无法考证,但早在街机游戏时代,尽管游戏中的人物由于机能限制,只能以简陋的像素图形呈现,但游戏海报本身便早已带上了色情属性:性感的女性角色身体和强健的男性角色肌肉,是能够最直接地招徕玩家的方式。新的技术作用于游戏,使得玩家的游玩体验和审美体验在获得极大提高之余,能够在游戏中发掘出新的乐趣——当然,这种乐趣也不乏高明的创造,但十有八九都会与色情扯上关系。有时制作者会理解玩家的想法,从而迎合玩家的心理为游戏嵌入新的功能(比如《战神4》或《蜘蛛侠》中的拍照模式);而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结果都是制作者低估了玩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一个例子可以看出色情要素是如何在游戏中发挥作用的。早在《死或生》中,软色情要素就被制作组当作一种差异化战略提出:《死或生》立项的初衷是要模仿当时大火的《VR战士》和《铁拳》,制作一款独特的3D格斗游戏,Team Ninja小组选择将“性感”与“暴力”两种元素合二为一,创作一款既有性感辣妹、又能激烈格斗的游戏。这款游戏就是《死或生》:通过为女性的胸部提供单独的3D建模,辅以昂贵的SEGA Model 2街机基板,使得游戏中女性角色的胸部可以不断摇动。
 |
 |
 |
另一方面,既然游戏本身与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互动性,因此在游玩过程中玩家可以主动发现色情:《重制版》游戏本身的dlc之中为主人公提供新的装扮。而在steam的社区之中,人们更是可以轻易获取主人公的色情mod:这些mod包括主人公里昂和克莱尔的性感泳装等。甚至连游戏中对里昂穷追不舍的暴君也有自己的三角裤mod。这些mod的加入使得游戏制作者辛苦营造的恐怖气氛毁于一旦,游戏成了古堡之中的泳装派对。对色情元素的倾向成了贯穿在电子游戏中的潜文本。在辛苦编写的故事情节和精心制作的数码景观被消费殆尽之后,在游戏的世界中还有纯粹靠性本能驱使的乐趣。乔治•巴塔耶认为,色情与动物的性活动不同,因为人的性活动受禁忌限制,且色情领域是僭越这些禁忌的领域。色情的欲望是战胜禁忌的欲望。色情欲望意味着与人自身对立 。再也没有比在电子游戏内部空间进行色情性的开掘更加贴切的注释了。劳动的时间是和性爱的时间严格区分开来的;但游戏混淆了这种区分。在这里,色情成为了一种奖励的反馈。玩家必须调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耗费大量时间创作自己专属的色情素材。今日,当我们提到游戏的隐患时,忧心忡忡的家长们不仅会关注它的成瘾性,更会担心所谓的“学坏”——即游戏中的暴力或色情元素。但这里存在一个根本的误区:并不是因为游戏呈现了暴力或色情,而是游戏允许人们利用暴力与色情,并从这种互动中获得快感。游戏重制的身体是一个神话的过程。它像极了神话中的造人隐喻。起先是像素,后来是简陋的多边形,时至今日,已经是细节上尽善尽美的人体了。然而,再精细的人偶终究是人偶,最后堕落为性爱玩具。我们要问:作为游戏人物,他们的灵魂在哪里?可操作性是否真正解放了他们?如果一个游戏的乌托邦之中只有玩家自己凭借自由意志为所欲为,这是一个怎样的乌托邦?
四、总结:自由之国?奴役之路?游戏的交互属性使得它在诸种艺术形式之中是最特殊的。没有哪一种艺术形式——音乐或绘画,戏剧或小说——能够像游戏这样强调受众的亲身参与,也没有哪一种在诞生之初就已经把受众镌刻在了自己的基因里。但这些还不足以构成一个乌托邦。的确,电子游戏的重制是一个诱人的幻象。早期的街机电子游戏以每台街机在游戏之后所显示的排行榜为引,吸引人们反复重玩,这是现实逻辑;而今日之电子游戏已经借助于技术手段的更替,成功地制造了一个自洽的世界,使得人们可以在其中实现隐身。如果说游戏允诺了一个世界,那它也未必是一个乌托邦,更不是“自由王国” 。技术上的不断重制,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游戏自身的逻辑。我们已经拆解了虚假的扮演,无用的风景,还有事实上毫无产出的生产行为:这些要素与乌托邦的想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精妙的神话图景。我们甚至还没有讨论到粉丝消费、同人创作等问题,但今日蓬勃发展的电子游戏产业(包括电子竞技)之现实已经远远走在了理论前面。如同互联网刚刚问世之初,它的先驱者们对“地球村”的设想满怀憧憬之时,没人能想到今日它所造成的却是更加隔绝的信息孤岛。参考:[1] 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2]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2007年[3] 乔治•巴塔耶:《色情》,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2月第一版[4] 陈涛《电影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5] 游戏研究社:《2019年,谁才是P站最受欢迎的游戏角色?》2019.12.13 https://mp.weixin.qq.com/s/clVCs9h7F6aftYxbCkdWDg[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作者:钟天意,青年作家,独立书评人。目前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
在《魂斗罗》中,我们很难说游戏玩家“扮演”了游戏中的比尔和兰斯。因为游戏中的战斗事实上仅有移动和射击两种基本要素,而基于手柄所作出的简单动作无法对应现实战斗中的复杂状况。无论是环境还是操作都是高度符号化的。而如今,由于游戏机性能的进化,像《重制版》这样的游戏中可以加入更多功能,譬如角色可以和环境高度交互,做出更复杂的动作,策划更复杂的战术。这种复杂呈现出一种去符号化的倾向。当面对暴君的追杀时,你可以让里昂持枪将其射杀,也可以用闪光弹将其晃晕后逃走,甚至还可以挑战用匕首将其击杀。相对应的,操作必然变得日益复杂。可以预想,在VR技术全面普及和提升之后,手柄也终将进入博物馆,戴上VR头盔的玩家可以实现完全的去符号化,以等价的肢体动作(而非按键)来进行游玩。那么,是否说随着游戏性能的进步,玩家就可以逐渐实现扮演功能?我们需要考量另一个重要问题——视角。《生化危机2》采用了较为少见的第三人称追尾视角,而《重制版》在这一点上做了革新,采用了自《生化危机4》以来便一直沿用的越肩视角。这两种视角都不是第一人称,也就是说,游戏的作者刻意淡化了代入感;玩家并不是在“我即主角”的心理认同感之中进行游戏的,整个游戏中你所扮演的也并非里昂•肯尼迪。事实上,玩家在游玩中产生的情绪上的反射都源于对里昂这个虚拟形象的共情。更加真实的形容,是在游戏中存在着另一个看不见的主体:这个主体像傀儡师一样操纵着游戏中的主人公,玩家扮演的正是这个傀儡师,而手柄等输入端扮演的则是牵丝。从《魂斗罗》到《重制版》,这个逻辑从未有过更替,不过是牵丝机关变得更复杂罢了。那么,第一人称射击游戏(FPS)是不是最理想的扮演行为?看似如此,但这背后又有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事实上,这时你扮演的并不是人,而是悬浮在空中的一双手。这一点很好理解:譬如,在完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生化危机7》中,男主人公伊森就是一个没有身体的形象——从经济上考量,制作组只给了他一双足够写实的手而已。因为视角的限制,伊森(或玩家)并没有办法查看身体,所以看不见的身体也就没有建模的必要。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游戏中的另一位旁观者,你就会发现伊森只不过是一双悬浮在空中的手和一堆台词的组合——这一幕要比任何僵尸怪物都要恐怖得多。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同时也是最好的隐喻:在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一切细节都尽善尽美时,身体却被刻意地忽略了。二、电子风景:无用之物或他方世界詹姆斯•卡梅隆认为,“电影是一种‘现实的诱惑’,我希望能创造出细节丰富的完美影像,令观众感受‘真实’的电影世界,从而被其深深吸引。” 藏在这宣言措辞中的野心令我们震惊,因为创造影像在这里事实上等同于创造世界,而这原本是上帝的工作。今天,抛开如《星球大战》这样的好莱坞大片不谈,电子游戏中的风景的确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无论是《战神4》中壮美的北欧风光,还是《死亡搁浅》中辽阔的末世荒原,而且可以预见,未来游戏中的电子风景将会更加真实。特效的技术问题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我们要讨论的是:当一款游戏在不断地进行Remake时,游戏性的部分究竟获得了哪些改进?
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避免沦为单一的射杀丧尸,游戏中增添了大量解谜元素:游戏的主要舞台——浣熊市警察局被设计为一座古老的美术馆,其中隐藏着大量的秘密房间、机关门等怪诞的、完全与警察局功能无关的设备。里昂和克莱尔必须在阴暗可怖的警察局中一边为谜题寻找线索(否则便无法推进游戏),一边提防丧尸的威胁。不孚众望的《生化危机2重制版》(以下简称《重制版》)于2019年1月发行。游戏使用《生化危机7》同款引擎RE Engine打造,宣传语中写道:“经典的生存恐怖游戏正式重生”。有趣的是,似乎是为我上面的观点补充佐证,宣传语中还特地强调了Remake 与remaster的区别。在故事、玩法与场景上,《重制版》都忠实地遵循了原作,并没有作出任何颠覆性改编(如加入新人物、改变原游戏人物命运等)。《生化危机2》可在PlayStation、N64等平台上游玩,是当年游戏界当之无愧的霸主,也是整个电子游戏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而时隔二十年,《重制版》的平台已进化为PC(对配置要求较高)、PlayStation 4、Xbox One三个平台。平台的更新换代直观地反映了游戏性能的升级。一、交互之道:看不见的傀儡师正如前述,在围绕着电子游戏所塑造的种种当代神话之中,一个最常见的陈词滥调便是:“玩家可以扮演xxx,彻底沉浸在游戏世界之中/获得亲临实境般的享受”。但这个神话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对于“扮演”这个词,宣传者从来未费心力考证过其严谨性。首先,扮演离不开输入端设备。以早期的任天堂第一代家用游戏机FC(family computer)为例。标准的FC手柄只有10个按键,而在游玩《魂斗罗》时,只需按压其中的六个——上、下、左、右、A、B。如今,一台标准PS4手柄上有20个按键,在一款3A大作中,每一个按键都会派上作用,有时还要算上不同的排列组合,操纵方式也包括推拉、轻扫、倾斜、连击、长按等。